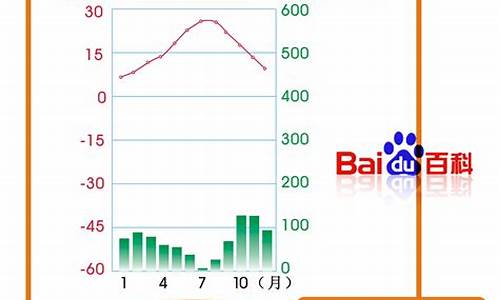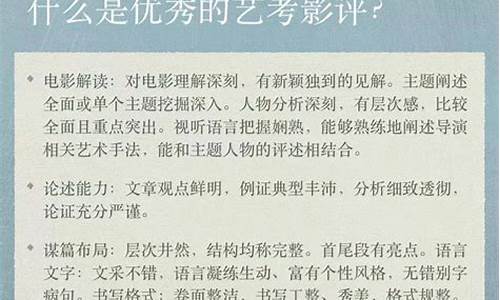对京剧评论的建议_对京剧的评论语
1.李丽芳的剧评
2.京剧为什么会“过时了”

京剧是艺术,但要活下来,必须定位为,民众,尤其是年轻的民众的选择太多,而民众的时间是有限,所有的活动都要争夺有限的时间,就是图个乐啊,不要太费劲,虽说付出幸苦打几十个小时拿到游戏目标也挺有成就感,但对于大众来说,肯定是费劲小刺激回报大的方式胜出,京剧和其他戏剧一样,都是科技局限时代的产物,你要讲一个故事,可以随意切换镜头、控制节奏、上特效,肯定比画花脸、固定唱腔的舞台戏剧更有表现力,所以京剧肯定输给**和MV这样现代的方式,而且,现代方式是在不断进化的,流行歌曲层出不穷,而京剧的唱法就是那样,拿固定去拼变化无穷,怎么可能赢。
李丽芳的剧评
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喜欢京剧?
1. 我觉得第一感觉就是听不懂,京剧中的特殊语音不能做到所有人都能入耳既懂。所以说单单只是好看,不能引起人们对京剧的兴趣。
2. 另外就是不懂故事,既然从头到尾都看不懂故事,又如何能让别人坚持看完呢?表演方式也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色,就像一百年后的人们看这个时代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。
3. 年轻人主张个性的张扬,喜欢鲜明激越的事物。而京剧有着很强的艺术性,也就是行当是很难改变的。这一点也算是老年人和年轻人最大的隔阂吧。
图为京剧
京剧为什么会“过时了”
宁夏京剧团的《杜鹃山》演出之后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李鸣盛扮演的乌豆,身高体壮,满脸络腮胡须,一戳一站,气宇非凡,唱念做打无不表现出一个草莽英雄的气概。《杜鹃山》在首都剧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1964年第7期《戏剧报》对宁夏京剧团的演出,发表了专题评论。文章说“宁夏京剧团的《杜鹃山》在忠实于原作基础上,根据京剧的艺术规律,对原作情节作了适当调整,创造出不同于话剧的京剧艺术形象”。“特别是由于演员在表演里充满了,对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笔酣墨饱、淋漓尽致。因此,整个的演出,给人以雄浑、豪放、粗犷和朴实的壮美的艺术感受。”文章评论李鸣盛的表演是这样写的:“饰演乌豆的李鸣盛同志,向以婉约、优美的唱工见长。他在刻画这一革命农民首领的性格时,从人物出发,大胆突破行当的局限,运用了花脸、武生、红净的表演,以期创造出革命的英雄形象。”在这次会演的会刊上,韩江水发表了题为“光辉的英雄形象”的剧评,文中说:“李鸣盛是余派老生,以擅唱闻名。为了演好乌豆,他大胆突破了行当,在不少地方,吸取了架子花脸的身段,糅合了铜锤和红生的唱腔。在唱、念、做、打诸方面,都能紧紧服务于刻画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性格与思想感情。如第一场,唱‘不怕高山千万丈,不怕河水万里长,只要找到***,赴汤蹈火又何妨’时,演员以刚劲有力的行腔,平起翻高,腔尾嘎然而止,铿锵有力。配合着粗犷、开阔的手势和身段,表现了人物坚毅、顽强的意志和追求党的坚定不移的决心。”
宁夏京剧团筹拍影片《杜鹃山》
1965年,农历乙巳年:宁夏京剧团筹拍影片《杜鹃山》
宁夏京剧团接到文化部指示,准备将《杜鹃山》一剧搬上银幕。很快长春**制片厂派来了以导演方荧为首的摄制组到银川,剧组昼夜不停加紧排练。准备工作已就绪,大队人马奔赴长春,而在途经北京的短暂停留期间,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,由于在上海负责京剧现代戏排练的,需要宁夏京剧团的演员李丽芳去上海京剧院《海港的早晨》(后改名《海港》)剧组担任主要角色,故此《杜鹃山》一剧的拍摄工作“暂缓进行”,结果最终未能成行。
《杜鹃山》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
1965年7月,农历乙巳年:1965年西北五省(区)戏剧会演举行
西北五省(区)戏剧会演在兰州举行。
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的《杜鹃山》在北京打响后,经过进一步修改,参加此次会演,李鸣盛饰乌豆,田文玉饰贺湘,田文玉饰杜妈妈,殷元和饰温七九子,徐鸣远饰老地保,舒茂林饰李石匠,刘顺奎饰郑老万。反响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加强烈,以致在宁夏京剧团观看其他兄弟团体演出的入场时刻,全场观众拍着手,齐声有节奏地向宁夏京剧团代表高呼“乌豆!乌豆!”。
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,京剧似乎都不是很景气。主要是因为中青年的观众、听众少了,多数青年观众不情愿买票进剧场。京剧被称为“老人的艺术”和“死不了、也好不了的艺术”。一些人感叹,京剧已经过时了。那么,京剧为什么会过时了呢?京剧真的已经过时了么?这十几年来,业内人士多从京剧艺术本身找问题,做改变。希望能让京剧艺术迎合时代的发展,吸引更多的青年观众,于是各种形式的新编剧目叠出,声、光、电齐上,加交响乐、拍电视片、改服(装)化(妆)道(具);中国人唱外国的事,外国人唱中国的事;不挂髯口的唱、不画脸谱的唱、不念韵白改道白、放弃程式弱化流派;“探索”、“创新”可谓旌旗招展,令人眼花缭乱。有位著名戏曲评论家这样说:“京剧艺术正在破茧重生,将逐渐告别旧的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,绽放新的光彩和魅力”。
京剧为什么会“过时了”?我觉得有内、外两方面的原因。
先说内因。近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批判和怀疑,从未停止过。清末民初,国家的落后挨打,使人们自然的开始对旧的一切进行重新的审视,从政治体制延伸至文化艺术。作为传统文化在舞台上的集大成者,京剧当然成了“旧”的代表和问责的对象。其实,早在那个时期,京剧就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,因为晚清的***酷爱京剧,很多艺人都成了经常进宫献艺的“内廷供奉”。所以,反清反帝就迁怒于京剧,京剧就成了某种象征,而当时京剧最为盛名的谭鑫培,他的唱腔就被讽为“亡国之音”和“靡靡之声”了。以来,不论左翼还是右派,从鲁迅、陈独秀到胡适等政治、文化名人,都一致地对京剧进行了指责和批评,继谭鑫培之后最为享誉的梅兰芳,也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。当时一些喜爱京剧的文人,在文章里就已经开始不约而同的预测,抒发着京剧必将走向灭亡的悲情。一些京剧工作者,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京剧进行改革,现在京剧新编戏里的“探索”和“创新”,在那时也屡见不鲜。从剧照上可以看到,梅兰芳在《黛玉葬花》里用了实景,《天女散花》和《洛神》里也融入了大制作布景和科技效果;除谭鑫培、梅兰芳外,谭富英、雪艳琴、言菊朋等名家也纷纷“触电”,把表演从舞台延展到银幕;在《纣王与妲姬》等新编剧目中,演妲姬的男旦干脆在舞台上袒胸露背来诱惑“纣王”,当然更是为诱惑观众和票房,不可谓不前卫了。很多现在新编京剧里的“新”,其实仍不过是早已尝试过而失败了的“旧”。正像《大师们的选择》里讲的那样,真正的艺术家最终还是回归了,而那些应景取巧的仍被淘汰。当然,回归不等于复古,在否定之否定后,京剧还是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。但京剧的理论工作,在其舞台实践最鼎盛时,却因为战乱和意识形态的纷扰而未能作一系统和规范的总结,成为“梅兰芳表演体系”的最大缺失。建国以后,京剧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、院团间的合作,使京剧得到了新的发展,除了老观众、老演员以外,也培养了一大批新观众、新演员。但不久,京剧艺术就再次成为新旧思想文化争论的焦点,剧目被大幅缩减(比如,最严重时程砚秋只能上演六个代表剧目)。传统戏再次成为旧文化、旧势力的象征。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,传统戏被现代戏取代,进而被“革命样板戏”所取代。京剧受到了思想改造,但也相当程度的保持了其传统的表现手法。这就是有人讲的:“‘革命样板戏’并没有让京剧艺术扭曲,反而拓展了新的题材”的原因。但是,人们当时并不会把“革命样板戏”改造上的成功归结为对传统程式的提炼和运用,而全当是“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在京剧艺术实践上伟大成果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京剧传统剧目开始解禁,而且越来越多,京剧艺术又有了回春的迹象。可好景并不长,八十年代中期以后,京剧很快就“过时了”,青年人更着迷于迪斯科、港台歌曲,剧场里呈现一片“白花花”的景象。有人完全归罪于外来文化的冲击,其实不完全对。试想,六十年代之前的中青年京剧观众,“”后都已是花甲上下了。而六十年代后的近二十年里,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砰击乃至批斗,不可能使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对传统文化艺术有多少亲切感,更谈不上教育、熏陶了。文化的断层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文化和思想的了解和尊重,也失去了对传统艺术的审美能力。这一辈人到“”后,正值青年。他们怎么可能走进剧场去聆听古代人物的“依依呀呀”呢?“孔老二”只会“三纲五常”,不懂民主、自由;老子道家就会作缩头乌龟和画符念咒,不讲发展、创新。失去传统底蕴的培养和熏陶,京剧魅力的光芒自然被遮蔽,这是八十年代后期京剧走向低谷的最大原因。换剧话说,不是京剧本身出了问题,而是京剧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土壤——民族传统文化价值,它出了问题。民族传统文化成了“老土”和“过时的”,那么它在舞台艺术的集大成者京剧,能不过时么?这不是去掉程式表演和掺进电子乐、交响乐就能解救的了的。把故宫的墙上都刷上立邦漆、贴上大理石,难道人们就会当它是帝国大厦吗?到九十年代末期,京剧的危机有所缓和。一方面,八十年代短暂的复兴,培养了一些青年的演员和观众;另一方面,随着“振兴京剧”和“音配像”及开设戏曲频道的陆续举措,为京剧整理了一些资料、提供了一些环境。但京剧市场的低靡并未改变。新世纪以来,随着传统文化的意识回归,我们终于理性的看待我们千年来的文化遗产,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。但丢失的荒废的,不可能在几天内、几年内重建和寻回。京剧仍不可避免的与时代一同浮躁着,急功近利、舍本求末、迎合铺张,都在“探索”、“创新”的大旗下张牙舞爪,而这些现象在京剧史上也并不稀奇。京剧是需要积淀和功力的,想速成为唯一方法就是对原有规则的重新洗牌,“推陈出新”、“破旧立新”、“变革维新”,又一轮的改造才刚刚开始呢。这次,有些人的创新比“样板戏”更彻底,既用时代意识改造京剧的思想,但摒弃了其传统的表现手法。其实,纯粹的、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,而再辉煌的拼凑和杂烩也会被历史遗忘。
再说外因。这一点已经被大家说得更多了,全球一体化逐渐显露成全球美国化,先进国家的文化似乎必然就是先进的。我们追捧美式的快餐、好莱坞的大片及衣、食、住、行的方方面面。同样,我们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艺术是否科学和国际化。但显然,我们眼中的国际化是不包括中国自己的,而我们也不去想这外来的科学标准是否又科学呢?西方人不信中医,我们的专家就呼吁取消中医的医学地位;外国人认为龙是凶暴不祥的,我们的专家就提议改变民族的图腾。幸而,外国人“喜欢”看昆曲听京戏、“喜欢”逛故宫串胡同。
我仿佛又偏激了。但偏激好像只是用来形容我的。你把京剧都改得不像京剧了,媒体也不说你偏激,因为你说:谁说京剧只能那个样儿的!?
我无言以对,叹声:京剧,“过时了”。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